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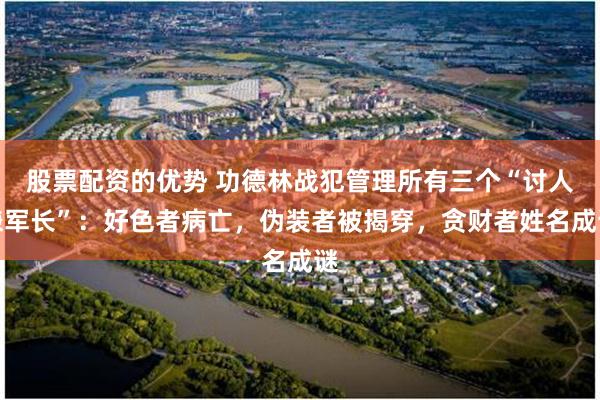
据原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的回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存在着一个微妙的鄙视链: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看不起非嫡系的杂牌军将领,杂牌军将领又瞧不起特务系统的牛字号股票配资的优势,而在特务系统内部,军统(保密局)出身的戴家班又对中统(党通局、内调局)的CC系嗤之以鼻。这个CC系指的是长期被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掌控的中统系统。
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们,即便在战败被俘后,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派系意识。他们将在战场上的对抗延续到了功德林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三三两两结成小团体,把昔日的战友当作对手,经常发生激烈的口角争执。有时候这种冲突甚至会升级为肢体冲突,比如军统出身的董益三(曾任军统局第四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少将处长)就曾当众扇了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一记耳光,把黄维打得一时发懵。等黄维反应过来要还手时,已经被众人七手八脚地拉开了。
展开剩余84%虽然这些来自不同派系的将领们平时互相倾轧,但在面对特定人物时,他们却能达成共识,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鄙视态度。在众多被同僚看不起的战犯中,有三个军长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的事迹在众人的回忆录中被反复提及,极尽嘲讽之能事。这种鄙视与派系无关,纯粹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不齿。
沈醉向来以圆滑世故著称,很少在公开场合批评他人。但面对那些品行特别恶劣的人,他也不吝于在回忆录中给予辛辣的讽刺。在战争年代,贪财、好色、虚伪这三种恶习尤为令人不齿,一旦被揭穿,就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最近有人撰文吹捧《潜伏》中被捕的九十二军副军长杨文泉(瑔),称其如何坚持原则、效忠蒋介石。但事实上,在功德林关押的一百多名国民党将领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为蒋介石成仁。被俘后,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将军们都变得异常温顺,没有人敢对管理人员大声呵斥,更不用说动手反抗了——这些行为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
那个被吹嘘为宁死不屈的杨文泉,实际上是最受同僚鄙视的战犯之一。原因就在于他过分好色,以及对自己外貌的过度关注。即便沦为战犯,他仍然保持着涂脂抹粉的习惯。由于无法获得正常的化妆品,他就想出了替代方案:每天洗脸要花上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还要涂抹雪花膏等护肤品,最后还要在头发上抹油——那是他用冬天防皴裂的蛤蜊油、甘油和凡士林调制的。他囤积大量凡士林的行为也引发了不少猜测,因为据说只有某些有特殊癖好的人才会常备这种东西。
这些美容用品散发出的气味自然不会太好闻。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留情地讽刺道: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他不像个军人,浑身散发着浓重的香气,还带着古代文人陆机《赴洛道中》描写的那种'顾影自怜'的酸腐气。总之,就是让人不舒服!一个战犯还整天油头粉面,恐怕是闻所未闻吧!这里说的味道并非指物理或化学意义上的气味,而是指从骨子里透出的令人作呕的气质。在整座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只有沈醉能勉强忍受和他说话,其他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这些见多识广的将军们倒不是对杨文泉有什么非分之想,而是担心杨文泉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奇怪的想法,光是想象就足以让人恶心好几天。
杨文泉在战犯管理所里整天把自己打扮得油头粉面、怪味熏天,比当年落入皇太极手中的洪承畴还要注重形象。指望这样的人能有骨气,那些吹捧他的作家恐怕也是被凡士林蒙蔽了心智。
杨文泉这种奇葩的爱好源于他极端好色的本性。沈醉评价说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反应,这个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他每到一地,就会不遗余力地追求当地的交际花、校花、名媛等社会上有名的美人,直到最终得手。杨文泉曾毫不掩饰地向沈醉传授他始乱终弃的秘诀:玩腻了想换口味时,只要吵几次架,再给一记耳光,对方马上同意离婚。之前排队等着的人会欢天喜地地接手,一点麻烦都没有。
沈醉对妻子相当忠诚,因此对杨文泉的所作所为极为不齿,对他的下场也带着几分幸灾乐祸:我越听越觉得恶心,像杨文泉这种人已经成了阶下囚,还沉迷于过去的罪恶。他率领的四川部队七十二军(戴笠坠机后,杨文泉获释晋升为七十二军中将军长、整编七十二师中将师长,这很可能是用军火商孙女那十万银圆的嫁妆买来的)在山东战场被俘时,是孤身一人,没有带随军家属。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也从未听说有家眷来看望他,这次可能是女方把他抛弃了。
除了好色的杨文泉,还有一个贪财的中将军长。沈醉戏称他为丢了牛还要捡绳子的贪婪之徒,此人是嫡系六十六军的军长,安徽合肥人。他的贪婪程度在国民党军队中堪称一绝:他从当连长时就开始吃空饷。他带的连队从来没有满编过,一方面是因为经常有人开小差或病故;另一方面是他故意不让满编,好从中渔利。从当连长时吃几个空饷,到当营长时吃十几个二十个,当团长、师长时越吃越多。当了军长后,更是变本加厉地大吃特吃。
沈醉在功德林见过这位六十六军的中将军长,所以他肯定不是该军最后一任军长罗贤达(罗贤达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沈醉是1956年才从重庆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不可能见到活着的罗贤达偷纽扣,也不可能亲耳听到罗贤达的偷窃理论:牛虽然丢了,但也要把牵牛的绳子捡回来,总比空手而归强。这位六十六军军长因为太过贪财,在功德林很不受待见。他刚在墙报上贴出一首诗,立即就有十多位将军撰文痛骂,最后骂得他只能躲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
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杜聿明、黄维等人都不太看重钱财,王耀武是通过正当生意赚钱而不吃空饷。像这种喝兵血的将军,走到哪里都会成为过街老鼠:要不是你们贪得无厌导致军心涣散,我们何至于在此相见?
六十六军军长偷纽扣的事在功德林传为笑谈,七十二军军长把自己活成了笑话,而第六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兵团司令部代参谋长娄福生则让一向乐观的沈醉都笑不出来:此人善于伪装积极,惯于损人利己,居然只比沈醉晚一年获得特赦。
如果说前两位军长因贪财好色而令人不齿,那么这位副军长则连沈醉都不得不佩服他的三点特质:一是脸皮厚,能把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或分走一半;二是表面装得比谁都卖力,实际上出力最少却喊得最响;三是管理人员在场时真干活,没人在场时就偷懒耍滑。沈醉已经够精明了,但娄福生比他更胜一筹。和娄福生合作,沈醉总是吃亏,从未占到便宜。
两人的第一次合作是洗被套。战犯们每两个月才洗一次被套,自然很不好洗。娄福生看新来的沈醉年轻力壮,就主动提出合作:沈醉负责搓洗,他负责交给洗涤组长验收。结果沈醉累得汗流浃背,受表扬的却是娄福生。沈醉又好气又好笑,想找机会报复,却始终算计不过娄福生。
后来功德林有时会组织战犯到农场劳动,沈醉起初还很得意:到农场劳动,娄福生应该找不到投机取巧的机会了。这可是实打实出力的活。没想到娄福生再次用他的聪明才智让沈醉吃了亏。
当时战犯们的劳动强度不大,主要是摘果子,不仅可以当场饱餐一顿,还能偷偷带些回去。沈醉武功不错,从小擅长爬树抓鸟捕蝉,爬树的本领远超常人,三五米高的果树三下两下就能爬到树梢。娄福生看中了沈醉的这个特长,又跑来合作:沈醉在树上摘果子往下扔,娄福生在地上捡起来装筐送到集中地。结果娄福生又因为摘得最多而受到表扬,沈醉只能在树上苦笑。
沈醉虽然笑而不语,但其他同学和管理员的眼睛是雪亮的。娄福生一贯的投机取巧最终被揭穿,不仅遭到众人鄙视,还受到管理员的批评。那是在农场修路时,大家一起拉石磙。有人肩膀都被麻绳勒肿了,娄福生却连汗都没出多少。一位与他同组的管理员当场批评他:喊得最起劲,拉得最不起劲,有时连绳子都没拉直。从此,娄福生的把戏被彻底揭穿,再也没受过表扬。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三个讨人嫌的军长中,好色的杨文泉没等到特赦就病死了;假装积极的娄福生特赦后鲜有人提及;而那个安徽合肥籍的六十六军军长究竟姓甚名谁,至今仍是个谜,用王耀武的话说就是知不道。
其实像这样贪财、好色、虚伪的军长股票配资的优势,在国民党军队中比比皆是。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恶习不改,弄得人见人嫌。蒋介石重用这样的人,其失败实属必然。读者们看完这三位军长的表现后,想必也有自己的看法:在您看来,这三种类型的战犯军长中,哪一种最令人厌恶?那位丢了牛也要捡绳子的军长,您知道是谁吗?
发布于:天津市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炒股期货配资_杠杆炒股票_鑫东财配资网观点